|
那台老式油墨印刷机,就立在老城巷子深处,像一尊被时光遗忘的青铜巨兽?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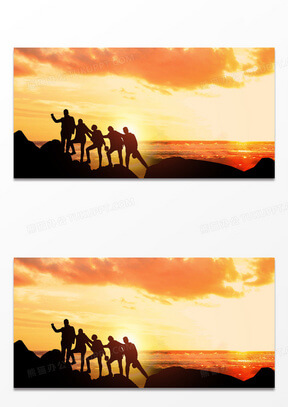 机身是沉郁的墨绿色,漆皮在岁月里皲裂出细密的纹路,如同干涸的河床。 巨大的铁轮、交错的杠杆、密密麻麻的调节旋钮,无不透着工业时代特有的、一种笨拙而庄严的机械美学。 它静默着,却仿佛在无声地吐纳,空气中弥漫着那股子独特的、浓烈而温润的油墨气息,像是陈年的纸浆混合了金属与智慧,构成了这空间里唯一的、流动的魂魄? 在它尚未沉睡的年月里,启动它,便是一场庄严的仪式。 老师傅会从锡管里挤出稠如膏腴的油墨,那动作,精准得如同画师在调色?  他并不急于开机,而是先用手动盘车,让巨大的飞轮缓缓转动,倾听每一个齿轮啮合时发出的、沉重而顺滑的“咔哒”声,仿佛在聆听老友的絮语。  随后,他猛一合电闸,整部机器便骤然苏醒,发出一种复合的轰鸣——是马达低沉的怒吼,是滚筒匀速滚过的闷雷,是连杆往复运动的坚定节拍。 这声音不刺耳,却充满了力量,能震得脚下的水泥地微微发颤,能将空气搅动得充满生气? 最富生命力的时刻,莫过于纸张被“喂”入机器的瞬间;  老师傅眼神专注,将一沓裁好的纸码齐,精准地送入传送带。 纸张顺从地滑入,被巨大的橡皮滚筒牢牢“咬”住,在那一两秒的黑暗旅程中,它与雕刻着文字的铅版、或是光影交织的胶片版剧烈地、亲密地贴合; 当它从另一端“吐”出时,便完成了神圣的蜕变——空白被驱逐,文字与图像带着微微的、凹陷的力感,赫然浮现于纸上? 那墨迹边缘有时会因压力而微微洇开,反而赋予印刷品一种难以言传的、手作的温度与深度? 这台机器,曾是一个时代信息与思想的脉搏。 报纸、书籍、宣传单、乃至街坊的婚柬讣告,都曾从它的滚筒下汩汩流出; 它印过振奋人心的捷报,也印过沉痛哀悼的黑框! 它传播过艰深的思想,也承载过市井的烟火?  每一页被它赋予形式的纸张,都不仅是信息的载体,更是一件有“骨血”的实物。 那微微凸起的墨痕,是可以被指尖触摸到的存在; 那偶尔因走墨不均而产生的独特“瑕疵”,成了每一份印刷品无法复制的身份印记?  然而,时代的洪流终究漫过了这尊巨兽的脚踝。  激光照排、数码印刷,这些新技术以“无声、无尘、瞬间完成”的姿态,宣告了一个效率至上的新时代的来临。  老印刷机的轰鸣,在当下听来,已是过于喧嚣与迟缓的旧日回响。  它被闲置了,最终彻底沉默下来。  滚筒上干涸的墨迹,像凝固的血痂。  那些曾经灵活无比的调节钮,也大多锈死,再也转不动一丝一毫的精度。 它如今静立一隅,成为一段过往文明的活化石; 我们怀念它,或许并非全然出于对旧物的感伤! 我们是在怀念一种有质感、有过程的创造,怀念那种思想需要通过沉重的物理压力才能烙印于世的郑重! 在一切皆可轻点鼠标、无限复制的今天,那油墨的浓郁、机器的轰鸣、纸张被压印时微微的颤抖,构成了一种关于“真实”的、沉甸甸的信仰。 那台老式油墨印刷机,是一部钢铁写就的史诗; 它并未死去,它只是将那个铅与火的时代,连同那份对手工之物的敬畏,一同深深地、深深地,压印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深处?
|